作者:xzy16888
2025/08/22首发于第一会所
字数:12255
上回书说到,穆桂英夜半书房之内,受贴身侍女春兰言语相激,勾起埋藏心
底三载之欲念火山,终致心神失守。
情潮翻涌如滔天巨浪之下,她竟取出深藏之羊脂玉势,自渎于此清静之地。
一番癫狂发泄,极乐之巅峰,恍惚间亡夫杨宗保温润面容竟猝然化作李元昊
那棱角嶙峋、鹰视狼顾之影像,如烧红的烙铁狠狠凿进其迷乱神思。
霎时间,灭顶羞耻与刻骨背叛感如万仞冰峰倾颓而下,顿将她由九霄快意云
端打入阿鼻地狱深渊。
书房之内,烛泪堆砌,狼藉遍染,唯余那曾经威震三军的巾帼女帅,半裸蜷
缩椅上,泪河决堤,灵魂似被抽空碾碎,只余一片白茫茫彻骨寒冰……正是:玉
峰陷落冰泉冷,铁誓崩摧孽海深。
欲知这番神魂俱裂之后,又生何等惊涛骇浪之变局,且容不才细细道来。
话说月坠西山,星隐层云。
穆柯寨后山峰顶,三层箭楼最高外廊,一袭藏青罗衣临风而立,正是穆桂英。
山巅罡风烈烈,卷得她衣袂狂舞,猎猎作响,更衬得身形孤峭挺立,直如崖
畔一株饱经风雷却犹自不倒之苍松。
然而细观其容,白日里端肃凌厉如开刃秋水之俊目,此刻却是眸光涣散,深
潭般沉静之下,涌动着只有天地幽谷方能容纳的滔天巨恸与无边倦意。
昨日书房疯狂,那焚身的烈焰已然冷却,徒余灼穿五脏六腑后的寒窟焦墟与
彻骨荒芜。
手中紧攥着一张被反复折叠、揉搓得几乎字迹模糊的陈旧战报,乃是半年前
杨宗保血染陷金、力敌至最后一刻之详细呈述。
指尖因过度用力而青白一片,指甲几欲刺破那薄脆的纸张。
指腹处传来粗粝的触感,那是沙场风霜与家国沉冤共同镌刻的印记。
「宗保……」一声破碎不成调的呼唤,如同濒死天鹅最后的哀鸣,溢出她苍
白干裂的唇瓣,瞬间被猛烈的山风撕扯得粉碎,未曾传远便已消散于茫茫夜色。
心口像是被那玉势硬生生剜去了一大块,空空荡荡,风从其中毫无阻拦地穿
过,带来冰锥刺骨般的痛楚与恐惧。
背叛。
对自己坚守半生的信念,对挚爱不渝的亡誓,对那顶天立地名节的一次彻彻
底底、鲜血淋漓的背叛。
纵然周遭万籁俱寂,无人觑见半分秘辛,然苍天在上,鬼神旁窥,她那双曾
令辽兵胆寒的纤纤素手,又如何还能有颜面再拉开那能百步穿杨的弓弦。
那根冰凉滑腻、裹满自身秽物的玉势,已化作一柄无形的利剑,悬于她道德
灵台之上,日夜切割,使她羞惭欲死。
自渎时最后一刻浮现的、李元昊那张深窝鹰目、浓髯虬劲的脸,更像一颗剧
毒的种子,深埋心底污秽的泥土中,令她浑身冰冷,汗毛倒竖。
那悬崖旁托举援手带来的些微暖意,此刻尽数化为跗骨的寒毒——此人究竟
是救命恩人,还是索命厉鬼?那刻意的亲昵揉捏,那目光里的灼热意味……莫非
是早已布下的陷阱?
汗,无声无息地从她光洁额头滑落颊边,被风抹去痕迹,唯留下那深入骨髓
的冷颤,证明并非全然的幻觉。
正当穆桂英神思煎熬,几被这灭顶的自责与惊疑拖入绝望深渊之时,在她视
域难及的极遥远之地,另一场暗流,正于更加黑暗深沉的幽冥中悄然涌动,其波
诡云谲之处,远比情欲焚身更能颠倒乾坤,倾覆山河。
此去西北三百里,一片荒沙戈壁深处,有座依黑水河而建的险要石堡,名为
「黑水寨」。
此处地势奇绝,四壁陡峭如刀斧劈斫,唯余一条羊肠石阶绕挂崖壁,端的是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绝险囚笼。
此处,正是囚禁掳掠而来的大宋天波府杨家众女之处。
此时节虽已近中秋,关外却苦寒刺骨,朔风呜咽着扫过嶙峋石壁,发出如夜
鬼悲哭的长号。
寨内几无灯火,唯最高一层那间石堡主室内,一支粗大的牛油烛,顽强地跳
跃着昏黄的豆光,映得壁上鬼影绰绰,狰狞乱舞。
烛光之下,一个身形消瘦的中年男子静坐石案之前。
此人颧骨高耸,瘦削脸颊深深凹陷,于枯槁面容上划出两道险峻的沟壑,恰
如这塞外的峡谷。
深陷的眼眶中嵌着一双细长眸子,此刻正凝神于手中一页墨迹淋漓的秘笺。
眼神幽深,精光内敛,似暗潭深水,表面静止,内里涡旋能吞没巨轮。
一身浆洗发白、略显松垮的西夏戎服罩在他身上,非但不显威武,反增几分
阴鸷鬼气。
此人正是李元昊最为信重、倚为心腹臂膀的首席谋士——没藏讹庞。
没藏讹庞,这位脸颊瘦削、颧骨高耸的西夏权谋重臣,正就着火光阅一封油
蜡封口的密札。
火光在他深陷的眼窝里跳动,映着一张常年浸淫于黑暗算计、已难觅丝毫人
气的脸孔。
石室里再无他人,唯有火焰的爆裂声与他枯骨般手指摩挲纸页的细微窸窣.
密札用的却竟是汉文,字迹龙飞凤舞,透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睥睨与急迫。
「没藏:杨家众妇押在你处,务必严封口舌,莫生枝节。
汴京线报,佘婆子失踪事已暗放风声,不日将沸扬汴京城。
此乃引信。
现着汝速遣心腹潜入汴梁,亲见庞藉,通陈要务:其一,言杨氏遗孀穆氏桂
英,与其寨中亲信暗通款曲,早有苟且之心。
此女守节兼守孝已是多年,其情状你我深知,今骤然淫乱,足见其志节败坏,
心生怨怼朝廷之意。
务必点明,此秘闻出自杨门内部,真伪自验。
其二,杨门第四代杨文广,小儿辈尔。
怯懦无能,骄纵无行,乃十足纨绔,不足深虑。
此点可安庞相之心,助其决断。
时机一到,吾将令边陲之兵佯攻穆柯寨左近宋之关堡,围而不克,专掠疲敝
宋兵弱旅。
此乃『疲宋』之计。
依赵宋庙堂习性,杨家此番获罪,虎落平阳,必遭漠视,宋军自保犹恐不及,
焉肯救匪?唯太祖遗脉八贤王赵德芳,性情刚直、惜才如命,必感念杨家昔日忠
义,出头提议令穆桂英戴罪立功,统兵解围。
待赵德芳开言,须力劝庞藉即刻出班力陈:一曰穆氏之秽行,背夫叛节已是
失德,今欲掌兵复权,焉知其非已是心怀怨怼?
其一,予以兵权,实乃宋廷大忌。
其二,依腐儒之言,常云三从四德者,其人不守妇道,能守臣道乎?众口铄
金,必不可矣。
二曰穆柯寨踞守险隘,其头领穆羽乃前汉老人,朝廷号令难下,早已形同割
据。
西夏强兵围其山寨而疏于攻打,反专剿远道宋军疲卒,此獠分明意在借刀杀
人。
假外敌之手削弱宋边诸军,其心可诛。
此乃驱虎吞狼,意在夺宋山陲掌控之权。
三曰上上策:即令穆柯寨自行抗敌。
朝廷坐观。
彼寨若败亡,削除割据隐患,西夏亦损兵折将;彼寨若守成坚勇,一则证其
忠心,二则可耗西夏精锐,朝廷乘其疲弊再遣精锐收拾残余,或可一举扭转颓势,
收渔翁之利。
故曰『坚壁清野,推虏攻寨』。
此策名正言顺,坐收实利,亦可名正言顺隔绝穆桂英兴复门楣之想。
彼酋赵祯向来优柔,必举棋不定。
如此,只需再劳庞贵妃于枕畔密陈「金匮遗盟」及八贤王金锏之事,则大事
可成矣。
若计成,赵德芳保穆桂英起复之言必遭重挫失势,庞藉可顺势掌控局势,打
击政敌根基。
此计与我与他几无妨碍,庞藉与我互相利用,于宋无害,于彼有利,当可行
矣。
此事关涉吾之大计,务必办得密不透风。
若穆柯寨捷报传来,亦当尽力阻碍,勿使宋廷兵马援其一粒米、一张弓。
切记,坐实『坚壁清野』之策。
静待吾下一步军令。」
没藏的眼神逐行扫过,时而微凝,时而闪过一丝了然的冷光,最终尽归于一
片沉冷的算计。
他读完,未置一词。
只将那密札凑近跳跃的火焰。
火舌贪婪地舔舐着薄薄的纸张,卷起的焦黑边缘急速蔓延,将那些带着血腥
气的图谋、那些指向汴梁大宋朝堂的毒箭焚烧殆尽。
顷刻间,密札便化为一撮轻薄的黑灰,飘落在他脚前的粗粝石地上。
未燃尽的火星在灰烬中明灭了一瞬,亦归于沉寂,只留下空中弥漫的短暂焦
糊气息。
「来人。」没藏讹庞的声音干涩沙哑,如同生锈的铁器刮过顽石。
一名身着西夏皮甲、面容隐藏在阴影里的心腹兵卒无声地闪入石室,单膝跪
地,静待吩咐。
「将此信。」
没藏从怀中取出另一封早已备好、同样蜡封的信函,递给兵卒,「务必亲自
交到汴梁城『聚宝斋』钱掌柜手中。不得经第二人手,亦不得拆看。若有半点差
池,提头来见。」
「遵命。」兵卒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双手接过那封似乎重逾千钧的信函,小
心收入怀中贴身处,再次无声地退了出去,融入石室外的黑暗甬道。
没藏讹庞枯坐灯下,火光将他嶙峋的影子投在凹凸不平的石壁上,扭曲拉长,
如同蛰伏的地底怪蟒。
他深陷的瞳仁里,仿佛倒映着千里之外汴京的巍峨宫墙、繁闹街市、暗流汹
涌的朝堂……嘴角,隐隐向上牵拉出一个冰冷的、几不可察的弧度。
李元昊这位殿下的棋,愈下愈险,却也愈下愈妙。
此番若能成事,则宋朝庙堂根基,又将摇动一分,殿下收服穆桂英一事,也
必将前进一大步。
石室重归寂静,只有外面传来的若有若无的痛呼和状似忍耐的撩人呻吟……
再说那汴京城内,朱雀门外。
虽值太平年月,贩夫走卒摩肩接踵,酒幡招展,丝竹盈耳,一派繁华盛景,
然则暗地里,总有那幽深府邸之内,秘事暗藏。
当朝太师庞藉府邸深处,一间暖阁陈设华美却不奢靡。
四壁书册罗列,博古架上玉器生光,俨然儒雅重臣之所。
然则此刻阁内气氛却沉凝如水。
檀香幽幽燃起,一缕淡烟攀缘而上,亦难驱散盘踞的肃杀之意。
庞藉坐在一张宽大的紫檀太师椅上,年过半百,鬓发微霜,一张脸保养得宜,
白净方正,眉眼间久居高位带来的雍容与深沉混杂着不易察觉的阴鸷。
他捏着方才由钱掌柜密呈而至的蜡封书信——那字迹狂放,正是没藏讹庞亲
书。
庞藉看得极为仔细,眉头时而紧锁,时而舒展。
信是用宋地白话书写,一目了然,却字字如针砭骨。
待到阅罢,他放下信纸,指尖在冰冷的紫檀木扶手上轻轻叩击,发出笃笃的
微响。
那平静的面容下,思绪却如急湍暗潮。
李元昊的心思,他岂能没有洞明?
佘太君一行不知所踪,自己前几日得密报,隐隐指向境外方向,如今李元昊
特意点明,无异于明示人质在手。
至于穆桂英与属下暗生情愫……哼,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即便是捕风捉影,
用在此刻,亦是妙哉。
此女悍勇刚烈,在民间声望极高,若有此污名加身,再煽动朝廷本就对杨家
叛国一事生出的忌惮疑惧,便是她浑身是胆、也是百口莫辩。
至于李元昊断言杨文广不成气候,这倒让他心中一块石头稍稍落地。
自己总有人走茶凉的一天,仇家后继无人,正合他的心意。
那设局的主意……庞藉眼底精光一闪而逝。
围点打援……驱虎吞狼……借刀杀人……环环相扣,竟是狠辣精准得要命。
由那小股西夏兵作饵,引动边境骚乱,料定其余宋军必然畏战不前,坐观成
败。
那好名惜才的八贤王赵德芳,岂能坐视穆柯寨陷落?必然跳出来请命穆桂英
戴罪平叛。
嘿,妙就妙在此时。
届时自己只需适时抛出那「暗生情愫」的流言蜚语,再点明穆柯寨经营日久,
形同坐拥私兵割据,此番西夏围而不攻专打朝廷兵马,岂非削弱朝廷对边境掌控?
如此一来,谁人又知这是不是穆柯寨和西夏演的一出戏!不如坚壁清野,让西夏
与穆柯寨火并……
一个可能失了名节、心怀怨望的妇人,与一群形同独立的寨兵……若能借西
夏之手除去,既可绝后患,省了朝廷动手的污名,又能极大削弱赵德芳在朝中的
号召力。
政争之事正是如此,一人进,就会有一人退。
那个手握金锏、太祖亲子的八贤王……这些年处处掣肘,是该好好敲打一番
了。
虽然不理解那李元昊为何总是抓着那杨家不放,但此计之下于己于国确实并
无损害。
一个元气大伤,人才凋零的杨家,哪里值得我庞太师计较,不过是和那李元
昊各取所需罢了。
至于陷害忠良的名声,呵!大丈夫生当五鼎食,死亦五鼎烹,不敢做桓温,
如何不能做主父偃!
庞藉沉吟片刻,指间的叩击声停。
他微微侧首,向侍立在一旁屏息凝神的儿子庞昱使了个眼色。
庞昱会意,悄然躬身退出暖阁。
不消两刻光景,侧门轻启,一阵香风率先涌了进来。
只见庞太师嫡女,当朝仁宗最宠爱的贵妃庞若雪,款步移入阁内。
她身量中等,却是生得玲珑有致,薄纱宫绡之内,腰如约素堪握,胸脯却丰
隆鼓胀出一道惊心动魄的弧度,其挺秀之势,竟将那薄薄的云罗撑显出极尽饱满
的浑圆印记。
下裳虽层层叠叠,但那宽而丰沛的雪股轮廓,依旧无法尽掩其极致的腴腆,
行动间,裙裾之下仿佛藏着两团浑圆的白玉脂膏,肉感沉甸甸地摇曳出无声波澜。
脸蛋儿是精雕细琢的端丽无双,肌肤白腻若初融新雪,一对剪水双瞳更是勾
魂摄魄,只是此刻那眼底深处潜藏的一丝机谋狡黠,令这天姿国色亦平添了几分
致命的危险。
「爹。」声音软糯娇媚,宛如清泉滑过丝缎。
庞藉并未起身,只示意了案上那封密信,「西夏那边来了消息。
你且看看。」他没有寒暄,直入主题。
庞若雪柳腰轻折,凑近书案,伸出葱管般的玉指拈起了薄薄的信纸。
她看得很快,眉梢眼底的风情随着信上字句悄然流转变化——惊诧、了然、
算计、狠绝……最终定格在一抹胜券在握的妩媚笑意上。
她阅罢,将信纸轻轻放回父亲手中,樱唇微启,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珠玑:
「爹爹以为如何?这步棋,确是绝妙。」
眼波流转,媚态中裹着冰霜般的决断,「八贤王爱惜羽毛,怜惜那穆桂英之
才,又自以为手握太祖金锏,总揽谏诤监察之权而矜傲自雄。此番穆柯寨有事,
他必作那仗义执言的君子状。只待他提了那贱人重掌兵权的话头……」
她微微一顿,眸光愈发灼亮锐利:「爹爹只需在朝堂之上,将李元昊信中所
言——无论虚实,只作流言汹汹、似有实据状,抛将出来。一个寡居守节却身染
桃色污名的寡妇,一个因丈夫『叛国』而备受苛责、心怀怨怼的悍妇,加上一个
拥兵自重形同自立的山寨。再将西夏围点打援专攻我朝军力的忧患点透。那坐在
龙椅上的官家,虽耳根子软,可最是忌讳此等威胁国朝根基之事。」
她轻轻嗤了一声,「如今杨家老幼不是流徙便是失落,只剩一根独苗杨文广
又不堪大用,早已不足为虑。然这穆桂英与穆柯寨,却是『尾大不掉』的变数。
朝廷能发落杨家满门,对这坐守边陲、军民一心的穆柯寨却束手束脚。如今西夏
愿做这把刀,父亲顺水推舟,正好借此良机剪除心腹之患,更可打压赵德芳日益
跋扈的锋芒。此一石二鸟,百利而无一害。」
庞藉捋须点头,眼中尽是嘉许的笑意:「吾女聪慧,深得吾心。
此事关键,却在陛下最后那一念之间。」他话锋一转,意有所指。
庞若雪了然一笑,娇媚天成中带着一丝冷绝的妖冶:「爹爹放心。待那朝议
纷争、龙心惶惑、摇摆难定之夜,自有女儿,将那临门一脚……轻轻补上。」
她葱白玉指轻轻抚过案上古琴紧绷的丝弦,发出极轻微却又极清晰的铮鸣。
汴京城的街市依旧嘈杂,人潮涌动,贩夫走卒的吆喝不绝于耳。
可没过几日,一种无形却沉重的阴霾,渐渐笼罩在有心人头上。
消息初起,只在几家深门大户的低语中流传。
接着,便像是投入了滚烫油锅的一滴水,轰然炸开,迅速蔓延至街肆坊间:
「听说了吗?天波府的佘老太君……杨家的那位定海神针……在前往穆柯寨的路
上……不知所踪了。」
「什么?消息确凿?」
「千真万确。有西边回来的商队亲眼所见,只说遭到了『强人』袭掠。」
「强人?哪路的强人敢动天波府的队伍?怕是……」
担忧、猜测、惊惶如野草般在汴京坊市疯长。
又过了不到一旬,更大的惊雷伴随着六百里加急的边报,炸响在皇城司的门
槛前。
八百里秦川古道,烽火连天。
西夏骑兵如一股股刮过草原的黑色旋风,越过那被视为壁垒的险要关隘,竟
直扑向边境一个并非重要军镇的方向——穆柯寨。
消息传到民间,瞬间点燃了早已绷紧的民情。
茶肆中、酒楼里、街角处,人声鼎沸:「西夏豺狼又来了。烧杀抢掠,无恶
不作。」
「这次怎地绕开州府不打,专冲着穆柯寨去了?」
「穆桂英。是杨门女将穆桂英。她还在穆柯寨。」
「西夏人恨杨家入骨。此番怕是冲着赶尽杀绝来的。」
「朝廷该发兵救援啊。穆元帅当年可没少杀退西夏人。是为国立过大功的。」
「哼。立大功?你没听说吗?杨家男的可是一窝子叛国贼。杨宗保就临阵反
了水。有其夫必有其妻。谁又能说得准?再说那穆柯寨孤悬在外,听说那穆桂英
寡居寂寞,准早就和她寨子里那些光膀子汉子眉来眼去了。朝廷若派兵,岂不是
去救一对……」有那早被收了钱的闲汉刻意压低却又引人耸听的声音在角落响起。
「放你娘的屁!」
立刻有粗豪的汉子拍案而起,怒目圆睁,「穆元帅何等英雄,镇守边关多少
次把西夏贼寇杀得屁滚尿流?岂容你等鼠辈在此污蔑!」
「就是。杨家满门忠烈,多少男儿血洒疆场?那杨宗保叛国之事扑朔迷离,
谁知是不是遭人构陷?佘老太君等人无故失踪,这其中没鬼?如今西夏摆明了冲
着唯一能打的杨门血脉穆元帅去了。朝廷若不救,岂不让天下忠勇之士寒心?!」
「话可不能这么说。那穆柯寨自立门头已经多少年了?俨然是个小朝廷。朝
廷的法度在山寨里行得通几分?说是杨家姻亲,可兵是他们的,粮是他们的,将
是他们的,除了名义上归宋,与割据藩镇何异?前唐殷鉴,犹不远矣啊。此番西
夏兵围点打援,专打我朝廷援军,分明是要借机削弱朝廷力量,让穆
柯寨彻底坐大。到时穆桂英一声号令,说自立投敌,谁人能挡?」
「没错。谁知道是不是那穆桂英心怀怨恨,私下勾连了外族,弄出这苦肉计
来骗朝廷出兵帮她火中取栗,反噬朝廷?」
「胡扯!简直是一派胡言!穆元帅忠心天下皆知。」
「知人知面不知心哪。一个女人,守孝多年,手握重兵……哼!」
民间舆论已沸,朝堂之上更是风雷激荡。
偌大的金銮宝殿,此时剑拔弩张,几乎要掀翻了穹顶。
八贤王赵德芳,这位太祖皇帝的嫡亲血脉,虽已年逾耳顺,然英气不减当年。
他头戴玄冠,身着紫蟒袍,手持象征太祖遗命、可上打昏君下责佞臣的金锏,
立于丹墀之下,腰杆挺直如同沙场的长枪。
他目光如炬,朗声奏道:「陛下。西夏不宣而战,兵锋直指我大宋边民。穆
柯寨虽为江湖之地,然寨主穆桂英系杨门嫡媳,为我大宋立下过赫赫战功。其部
曲多年抗击西夏,守土安民。此值家国危难之际,敌寇肆虐之时,岂可坐视孤寨
陷于豺狼之口而朝廷不发一兵一卒?臣恳请陛下。即刻下旨,赦免穆桂英待罪之
身,由其统领附近府军及自发义军,以迅雷之势反击西夏。一则扬我大宋国威,
震慑不臣;二则解穆柯寨之围,保我臣民。此举上应天心,下顺民意,望陛下明
鉴。」
声音如同洪钟大吕,在殿宇间回荡,许多武将脸上露出感佩振奋之色。
然而话音刚落,殿内那老成持重如岳峙渊渟的太师庞藉,不慌不忙地踏前一
步,躬身行礼,他声音不高,语速平缓,却字字带着千钧之力、浸透骨髓的寒意:
「王爷忧心国事,拳拳之心老臣感佩。然,」
他话锋一转,似带着无限惋惜与隐忧,「军国大事,非同儿戏,尤须审慎查
察,明辨主次。臣近日亦闻军报,西夏此次出兵,虽号称数千精骑,实则虚张声
势,主力并未越过我朝早已筑垒成墙的重镇险关。他们围住了穆柯寨,却并不急
于攻打,其主力反倒在我各卫所援军必经之路频频袭扰设伏。意图为何?此乃
『围点打援』之毒计。是要以穆柯寨为饵,诱我朝廷大军前赴,然后趁其疲惫分
路设伏,以求在平原旷野之上,削弱乃至歼灭我增援之精锐。」
庞藉抬起头,目光如霜刃般扫过八贤王,沉声道:「此其一。
再者,老臣不得不提那穆柯寨……恕臣直言,此寨自穆羽老寨主创立,众人
拥立,号「穆天王」,后为穆桂英经营,已历两代,数十年矣。
其拥精兵数千,粮秣自足,城坚寨厚,法令自设,军卒只知有寨主,不知有
朝廷。
名义上归附,然形同割据一方。
穆桂英身为朝廷侯爵,夫家又犯下叛国弥天大罪,获罪于朝廷,其本应深居
简出恪守本分,静待朝廷法断。
然其退守穆柯寨后,非但未尽分毫收敛请罪之意,反而似有加固城防、扩招
兵员之举。
此番西夏猝然相攻,兵锋所向,时机选择……岂不蹊跷?更兼坊间传言纷扰
……」他刻意停顿了一下,眼神显得凝重无比,「或有捕风捉影,言道其夫亡寡
居,于寨主之位统领男丁日久……难免有瓜田李下……暗生情愫之嫌……虽未入
罪,然民心已有疑虑。
此等情形下,其是否真如八爷所言,心怀忠君报国之念?抑或因身陷罪名而
心生怨怼?其麾下兵马,是否会为朝廷所用?抑或只效忠于穆寨主?老臣实不敢
妄自断言。」
他再次深深一躬,声音恳切却如重锤砸在仁宗心坎:「陛下。
若朝廷此刻贸然派遣大军救援,耗费钱粮无数、兵卒血肉之躯姑且不论,倘
若此女果真心怀异志,与西夏内外勾结,演一出苦肉计,那我增援大军岂不是自
投罗网、腹背受敌?届时非但救援不成,反使将士沦为鱼肉。
这后果之惨烈,非我大宋所能承受。」
他抬起头,眼中精光一闪而逝,抛出最终的狠棋:「依老臣愚见,不若反其
道而行之。
既然西夏觊觎的是我增援之军,穆柯寨又形同独立王国。
那便传令各处官军卫所,只加强险要关隘守卫,谨防西夏主力乘虚叩关。
至于穆柯寨方向……施行坚壁清野之策,将邻近寨子的军民尽数撤入坚城之
内。
既然西夏人如此『好意』地替我们去扫清那个朝廷多年想动而碍于颜面情分
又不好动手的『隐患』,倒不如……」他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顺水推舟,
隔岸观火。
让那如狼似虎的西夏军,去替朝廷『试探』一下穆柯寨的忠诚与实力。
若穆柯寨万众一心浴血奋战,挫败强敌,那自然是忠于朝廷、勇于担当的铁
证。
陛下不妨再予以褒奖安抚以安其心,朝廷威信无损,更可得一强援固守西陲。
若……他们不敌溃败,或被西夏所灭,或选择从了西夏……」他冷哼一声,
话中寒意砭骨,「那不过是证明了其早有异心或实力不济,朝廷亦省去了一个心
腹之患,更借此昭告天下有异心者,不念朝廷体统、行割据之实者,便是如此下
场。
此乃一举数得、以静制动的上上之策。
望陛下……明断乾坤。」
「庞藉。
尔……尔敢妄揣忠良,信口雌黄!」八贤王须发怒张,手中金锏直指太师,
声若雷霆,「穆元帅为国血战之时,尔等尚不知在何处安享太平。
杨家满门忠骨埋在疆场。
此等污蔑构陷,岂是士大夫所为?分明是坐视忠良被戮,行那亲痛仇快之事。
更欲借此打压异己,其心可诛!陛下,万万不可听此祸国之言!」
「王爷。」庞藉不卑不亢,针锋相对,「此非老臣一己私见,而是为社稷安
危计,为万千军士性命计,为朝廷纲纪计!岂能将我大宋精锐,置于一个名节存
疑、立场难明的戴罪之身手中?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岂能如此轻率?至于杨家过往忠烈与否……功过自有后世评说。
然今日之事,关乎当前之国策。
容不得半分私情。
王爷怕是爱才心切,恐为情所蔽,反中敌寇奸计。
陛下圣明烛照,当知其中轻重。」
殿中双方唇枪舌剑,势同水火。
仁宗皇帝赵祯高踞龙椅,眉头紧蹙,脸色白一阵红一阵。
一面是皇叔据理力争,慷慨激昂,以国威民心为说辞;一面是国之重臣老谋
深算,字字不离社稷安危、朝廷利益,处处点中他内心最深的疑惧与忌讳。
他欲反驳庞藉,又觉得其所言似乎稳妥;欲支持赵德芳,又怕真如庞藉所料
酿成巨患。
尤其那「穆桂英心怀怨怼」与「穆柯寨形同割据」的利刃,一次次精准无误、
不疾不徐地切割着他那本就犹豫不决的心弦。
满朝文武鸦雀无声,目光俱都聚焦在御座之上,连呼吸都屏住了一半,唯恐
错过圣心丝毫的偏移。
朝堂内外的空气,仿佛凝固成一块巨大沉重的冰坨子,压得人喘不过气。
这一日的朝会,便在剑拔弩张又诡谲难言的死局中勉强落幕,未能议决。
是夜。
九重宫阙深处,椒房别院。
月光透过轻绡宫纱,映在描金剔红的妆台上,也映着庞贵妃一张精心养护、
艳若桃李的脸庞。
宫苑内的奇花异草吐纳幽香。
她一身浅碧色薄绸寝衣,那丰满到足以令金吾侧目的傲然胸乳将前襟绷显出
一道惊心动魄、浑不似人间能有的饱满曲线,顶端两抹深壑在幽暗烛光下若隐若
现。
窄软的腰肢束以轻柔丝绦,纤韧欲折。
寝衣下并无重裙,其下身段的丰盈轮廓毫无遮掩,尤其从后腰至玉臀的曲线,
宛如精心塑成的白腻山峰,宽厚而腴美,沉甸甸地坠出两团令人心荡神驰的绝世
峰峦。
莲步轻移间,股肉微微颤晃,那惊心动魄、充满原始生命韵致的丰腴颤意,
便是最严苛的礼法官在此,也难免多看一眼那亵越宫规的美好弧度。
她捧着一只玲珑嵌玉的鎏金汤碗,步履轻盈地行至御榻之前。
汤盏里盛着温热的冰糖雪蛤莲子羹,蒸腾的热气带着甜香,缭绕在她粉雕玉
琢的颈侧耳垂。
榻上的仁宗刚从繁冗的朝议中脱身,此刻正斜倚着金线蟒纹的引枕,揉着发
胀的额角,眉心紧锁。
「官家……」庞贵妃声音甜腻得如同浸了花露,轻轻坐上榻沿。
那惊人的臀肉随着她落座的姿态,沉甸甸地陷入软褥之中,又因那柔韧十足
的弹性,微微向四周延展出饱满丰盈的光晕,寝衣紧贴处,弧线勾魂摄魄。
她将玉碗送至仁宗嘴边,纤纤玉指拿起调羹,姿态优雅又体贴。
「白日朝堂议事实在惊心动魄,伤了神思。快用些羹汤定定神。」
仁宗就着她的手啜了一口,温热甜润的汤汁滑入喉咙,稍缓烦忧。
他叹息一声:「爱妃啊,这穆柯寨之事……朝上纷议汹汹,实在是难以决断。」
庞贵妃放下羹碗,抬起柔若无骨的皓腕,用温软的指尖轻轻揉按仁宗的太阳
穴,动作娴熟。
她微微倾身,饱满的胸乳几乎蹭到仁宗的臂膀,温热的馨香包裹着帝王。
「妾身一介女流,不敢妄议前朝政事,」
声音放得极轻极柔,如同枕边呢喃,带着些许委屈又识大体的娇态,「只是
……只是看着官家忧心如焚,妾身这心里也七上八下……想到那八贤王……」
她巧妙停顿,似是无意提起,美目中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锋芒。
「他今日在朝堂之上,手持太祖金锏,言辞激烈……似乎有些过于……咄咄
逼人了。」
她叹了口气,指压动作未停,眼神带上几许迷惘与忧惧,「那金锏之威……
唉,妾身每每想起便心惊肉跳。太宗皇帝传下它,自然是赋予宗庙社稷之重托。
可……可王爷身负太祖血脉,又掌如此神器……这些年每每遇事则直言强谏……
对官家的圣裁,也……也时有争持……」
她小心翼翼地看了仁宗一眼,见他并未动怒,反而眉头蹙得更深,才接着用
那气若游丝、仿佛只诉与榻上情郎听般的声音,低低道:「妾身有时……夜深人
静想起那金匮盟约前事……便止不住地害怕……」她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仿佛
深陷噩梦,那双会说话的眸子里盈满了惊悸的泪光,「官家您是太宗皇帝嫡传的
龙子,承的是天授的正大统序。可……可太祖当年亦是传位于弟才留下那金匮之
盟……每每思及于此……」
她声音哽咽,更显楚楚可怜,「妾身只是忧心官家。忧心这大宋的万里江山。
若事事都由八贤王执了金锏说了算……那圣上……这天下究竟系于谁人?」
这番话如同淬毒的冰针,轻柔却无比精准地刺入了仁宗心底最深的角落。
那丝早已盘踞多年的、难以启齿的、基于金匮之盟阴影的忌惮与恐惧,瞬间
被无限放大。
太祖之死、兄终弟及的历史、八叔手中的金锏……这一系列联想组合成的恐
惧,远远超过了此刻边境穆柯寨的得失,更深沉地压在了赵祯的心头。
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一股寒意从脊椎骨升起。
「够了。」仁宗猛地低喝一声,挥开庞贵妃的手,脸上阴云密布。
他并非喝斥爱妃,而是那骤然爆发的对自身权威的强烈恐慌与不安。
庞贵妃这看似关切、不着痕迹的「忧虑」,恰如一瓢滚油泼在了本就暗火丛
生的薪堆之上。
庞贵妃立刻噤声,盈盈起身,跪俯在榻前,云鬓微乱,体态显得更加楚楚可
怜,玲珑曲线在跪姿中愈发抖落惊心动魄的饱满与委屈:「陛下息怒。是臣妾多
嘴了。臣妾妇人之见,胡言乱语不识大体……」
她深深叩首,额头几乎触地,肩背微微颤抖。
那惊心动魄的腰臀线条在伏低的姿态中构成一弯极其夸张的、蕴含了巨大绵
软弹力的硕美弧线,带着无声的娇弱哀求之意。
仁宗看着跪地的尤物,心头的火怒与那丝被触及敏感地带的惊悸纠缠着,最
终化为一声不耐烦又意蕴不明的冷斥:「后宫切勿干政。这等话,休要再提。」
「妾身知罪。」
庞贵妃如蒙大赦,又惊又喜地抬起头,泪光莹莹中带着无限的信服仰慕,
「官家……妾身知道错了……」
她膝行一步,柔若无骨地倚在榻边,重新将那碗温热的羹汤端起,乖顺地奉
上。
只是方才那番诛心之言,已如毒蛇噬髓般,牢牢印在了仁宗心头最敏感的所
在。
次日早朝。
龙椅之上,仁宗的神色似乎比昨日更显疲惫憔悴,眼下带着微青。
他目光扫过阶下,刻意避开了八贤王那殷切又锐利的眼神。
朝堂之上再次陷入关于穆柯寨与西夏兵锋的廷议激辩。
八贤王依旧据理力争,激昂慷慨,字字掷地有声。
庞藉一派则反复申明「保存实力」、「防范内患」、「以夷制异」之利。
待到双方辩无可辩,仁宗沉默良久,终于开了金口,声音带着一丝难以掩饰
的沙哑与疲倦:「众卿所言……朕已细思。事关重大,牵涉国本安危,不得不慎
之又慎。」
他微微一顿,殿内落针可闻。
「穆柯寨……」
提到这个名字,仁宗眼神闪过一丝复杂难辨的光,「穆桂英虽承其父旧业,
又曾立战功,然其夫杨宗保犯有重罪,其身为待罪之臣妻室,身份敏感。加之地
处边陲,兵员复杂。值此西夏兵锋汹汹而来之时,贸然大举增援,恐堕敌围点打
援奸计之中。此其一。」
「其二。」
他避开八贤王灼灼的目光,语速加快,仿佛急于摆脱某种无形的压力,「穆
柯寨城坚寨深,兵勇尚在。值此国难之际,正需其上下同仇敌忾,固守家园,以
彰忠烈,亦为朝廷分忧。」
他深吸一口气,最终定下调子:「颁朕旨意:明旨褒扬穆柯寨众将士守土抗
敌之功。」
「命邻近州府官军,固守险要关隘要冲,绝不可使西夏一兵一卒得以突破防
线南下,威胁百姓安宁。然……非奉明确诏令,不得擅离驻防之地,随意出击浪
战。更不可赴援穆柯寨,堕敌奸谋。」
「令穆柯寨寨众,戮力同心,固守疆界。待其自保成功,朝廷……自有后续
安抚,钦此。」
这旨意一出,殿内群臣反应各异。
八贤王面如死灰,手握金锏的指节捏得发白。
那最后那句「待其自保成功,朝廷自有后续安抚」,听在他耳朵里,与判了
穆柯寨上下无援待毙的死刑何异?这分明是采纳了庞藉隔岸观火、坐视自生自灭
的毒计。
甚至,还裹上了一层褒奖守土的糖衣。
其无情之至,何其寒凉。
庞藉一派,则是眼观鼻鼻观心,垂首恭贺圣裁英明。
庞藉本人心中雪亮,昨夜那双纤纤玉手点下的「棋眼」,已然生效。
陛下心中那只名叫「猜忌」、「忌惮太祖一脉夺权」以及「对割据势力深深
戒备」的猛虎,终于在庞贵妃那滴「忧惧之泪」的催化下,挣脱了最后一丝人情
束缚,咆哮而出了。
旨意如风,迅疾地自崇政殿传出,由门下省覆核,再由内侍誊写盖上天子玉
玺宝印。
随即,一骑披着朝廷紧急边报绶带的传旨使者,马蹄扬尘,在薄薄的晨曦中
冲出巍峨的汴梁西华门。
马蹄踏碎了官道上凝结的薄霜,一人一骑,绝尘向西。
目标只有一个——远在数百里之外,或许此刻已被战云笼罩的穆柯寨。
这位不知使命轻重的传旨使者,并不知道怀中这道贴着冰冷鹞羽、火漆封口
的诏书,将会在数日之后,如何残酷地撕裂千里之外一束坚守的信念,又将这滚
滚狼烟的走向推向何等血腥残酷的境地。
他只知道,要鞭打快马,奔向那片即将迎来最终拷问的战火之地。
2025/08/22首发于第一会所
字数:12255
上回书说到,穆桂英夜半书房之内,受贴身侍女春兰言语相激,勾起埋藏心
底三载之欲念火山,终致心神失守。
情潮翻涌如滔天巨浪之下,她竟取出深藏之羊脂玉势,自渎于此清静之地。
一番癫狂发泄,极乐之巅峰,恍惚间亡夫杨宗保温润面容竟猝然化作李元昊
那棱角嶙峋、鹰视狼顾之影像,如烧红的烙铁狠狠凿进其迷乱神思。
霎时间,灭顶羞耻与刻骨背叛感如万仞冰峰倾颓而下,顿将她由九霄快意云
端打入阿鼻地狱深渊。
书房之内,烛泪堆砌,狼藉遍染,唯余那曾经威震三军的巾帼女帅,半裸蜷
缩椅上,泪河决堤,灵魂似被抽空碾碎,只余一片白茫茫彻骨寒冰……正是:玉
峰陷落冰泉冷,铁誓崩摧孽海深。
欲知这番神魂俱裂之后,又生何等惊涛骇浪之变局,且容不才细细道来。
话说月坠西山,星隐层云。
穆柯寨后山峰顶,三层箭楼最高外廊,一袭藏青罗衣临风而立,正是穆桂英。
山巅罡风烈烈,卷得她衣袂狂舞,猎猎作响,更衬得身形孤峭挺立,直如崖
畔一株饱经风雷却犹自不倒之苍松。
然而细观其容,白日里端肃凌厉如开刃秋水之俊目,此刻却是眸光涣散,深
潭般沉静之下,涌动着只有天地幽谷方能容纳的滔天巨恸与无边倦意。
昨日书房疯狂,那焚身的烈焰已然冷却,徒余灼穿五脏六腑后的寒窟焦墟与
彻骨荒芜。
手中紧攥着一张被反复折叠、揉搓得几乎字迹模糊的陈旧战报,乃是半年前
杨宗保血染陷金、力敌至最后一刻之详细呈述。
指尖因过度用力而青白一片,指甲几欲刺破那薄脆的纸张。
指腹处传来粗粝的触感,那是沙场风霜与家国沉冤共同镌刻的印记。
「宗保……」一声破碎不成调的呼唤,如同濒死天鹅最后的哀鸣,溢出她苍
白干裂的唇瓣,瞬间被猛烈的山风撕扯得粉碎,未曾传远便已消散于茫茫夜色。
心口像是被那玉势硬生生剜去了一大块,空空荡荡,风从其中毫无阻拦地穿
过,带来冰锥刺骨般的痛楚与恐惧。
背叛。
对自己坚守半生的信念,对挚爱不渝的亡誓,对那顶天立地名节的一次彻彻
底底、鲜血淋漓的背叛。
纵然周遭万籁俱寂,无人觑见半分秘辛,然苍天在上,鬼神旁窥,她那双曾
令辽兵胆寒的纤纤素手,又如何还能有颜面再拉开那能百步穿杨的弓弦。
那根冰凉滑腻、裹满自身秽物的玉势,已化作一柄无形的利剑,悬于她道德
灵台之上,日夜切割,使她羞惭欲死。
自渎时最后一刻浮现的、李元昊那张深窝鹰目、浓髯虬劲的脸,更像一颗剧
毒的种子,深埋心底污秽的泥土中,令她浑身冰冷,汗毛倒竖。
那悬崖旁托举援手带来的些微暖意,此刻尽数化为跗骨的寒毒——此人究竟
是救命恩人,还是索命厉鬼?那刻意的亲昵揉捏,那目光里的灼热意味……莫非
是早已布下的陷阱?
汗,无声无息地从她光洁额头滑落颊边,被风抹去痕迹,唯留下那深入骨髓
的冷颤,证明并非全然的幻觉。
正当穆桂英神思煎熬,几被这灭顶的自责与惊疑拖入绝望深渊之时,在她视
域难及的极遥远之地,另一场暗流,正于更加黑暗深沉的幽冥中悄然涌动,其波
诡云谲之处,远比情欲焚身更能颠倒乾坤,倾覆山河。
此去西北三百里,一片荒沙戈壁深处,有座依黑水河而建的险要石堡,名为
「黑水寨」。
此处地势奇绝,四壁陡峭如刀斧劈斫,唯余一条羊肠石阶绕挂崖壁,端的是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绝险囚笼。
此处,正是囚禁掳掠而来的大宋天波府杨家众女之处。
此时节虽已近中秋,关外却苦寒刺骨,朔风呜咽着扫过嶙峋石壁,发出如夜
鬼悲哭的长号。
寨内几无灯火,唯最高一层那间石堡主室内,一支粗大的牛油烛,顽强地跳
跃着昏黄的豆光,映得壁上鬼影绰绰,狰狞乱舞。
烛光之下,一个身形消瘦的中年男子静坐石案之前。
此人颧骨高耸,瘦削脸颊深深凹陷,于枯槁面容上划出两道险峻的沟壑,恰
如这塞外的峡谷。
深陷的眼眶中嵌着一双细长眸子,此刻正凝神于手中一页墨迹淋漓的秘笺。
眼神幽深,精光内敛,似暗潭深水,表面静止,内里涡旋能吞没巨轮。
一身浆洗发白、略显松垮的西夏戎服罩在他身上,非但不显威武,反增几分
阴鸷鬼气。
此人正是李元昊最为信重、倚为心腹臂膀的首席谋士——没藏讹庞。
没藏讹庞,这位脸颊瘦削、颧骨高耸的西夏权谋重臣,正就着火光阅一封油
蜡封口的密札。
火光在他深陷的眼窝里跳动,映着一张常年浸淫于黑暗算计、已难觅丝毫人
气的脸孔。
石室里再无他人,唯有火焰的爆裂声与他枯骨般手指摩挲纸页的细微窸窣.
密札用的却竟是汉文,字迹龙飞凤舞,透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睥睨与急迫。
「没藏:杨家众妇押在你处,务必严封口舌,莫生枝节。
汴京线报,佘婆子失踪事已暗放风声,不日将沸扬汴京城。
此乃引信。
现着汝速遣心腹潜入汴梁,亲见庞藉,通陈要务:其一,言杨氏遗孀穆氏桂
英,与其寨中亲信暗通款曲,早有苟且之心。
此女守节兼守孝已是多年,其情状你我深知,今骤然淫乱,足见其志节败坏,
心生怨怼朝廷之意。
务必点明,此秘闻出自杨门内部,真伪自验。
其二,杨门第四代杨文广,小儿辈尔。
怯懦无能,骄纵无行,乃十足纨绔,不足深虑。
此点可安庞相之心,助其决断。
时机一到,吾将令边陲之兵佯攻穆柯寨左近宋之关堡,围而不克,专掠疲敝
宋兵弱旅。
此乃『疲宋』之计。
依赵宋庙堂习性,杨家此番获罪,虎落平阳,必遭漠视,宋军自保犹恐不及,
焉肯救匪?唯太祖遗脉八贤王赵德芳,性情刚直、惜才如命,必感念杨家昔日忠
义,出头提议令穆桂英戴罪立功,统兵解围。
待赵德芳开言,须力劝庞藉即刻出班力陈:一曰穆氏之秽行,背夫叛节已是
失德,今欲掌兵复权,焉知其非已是心怀怨怼?
其一,予以兵权,实乃宋廷大忌。
其二,依腐儒之言,常云三从四德者,其人不守妇道,能守臣道乎?众口铄
金,必不可矣。
二曰穆柯寨踞守险隘,其头领穆羽乃前汉老人,朝廷号令难下,早已形同割
据。
西夏强兵围其山寨而疏于攻打,反专剿远道宋军疲卒,此獠分明意在借刀杀
人。
假外敌之手削弱宋边诸军,其心可诛。
此乃驱虎吞狼,意在夺宋山陲掌控之权。
三曰上上策:即令穆柯寨自行抗敌。
朝廷坐观。
彼寨若败亡,削除割据隐患,西夏亦损兵折将;彼寨若守成坚勇,一则证其
忠心,二则可耗西夏精锐,朝廷乘其疲弊再遣精锐收拾残余,或可一举扭转颓势,
收渔翁之利。
故曰『坚壁清野,推虏攻寨』。
此策名正言顺,坐收实利,亦可名正言顺隔绝穆桂英兴复门楣之想。
彼酋赵祯向来优柔,必举棋不定。
如此,只需再劳庞贵妃于枕畔密陈「金匮遗盟」及八贤王金锏之事,则大事
可成矣。
若计成,赵德芳保穆桂英起复之言必遭重挫失势,庞藉可顺势掌控局势,打
击政敌根基。
此计与我与他几无妨碍,庞藉与我互相利用,于宋无害,于彼有利,当可行
矣。
此事关涉吾之大计,务必办得密不透风。
若穆柯寨捷报传来,亦当尽力阻碍,勿使宋廷兵马援其一粒米、一张弓。
切记,坐实『坚壁清野』之策。
静待吾下一步军令。」
没藏的眼神逐行扫过,时而微凝,时而闪过一丝了然的冷光,最终尽归于一
片沉冷的算计。
他读完,未置一词。
只将那密札凑近跳跃的火焰。
火舌贪婪地舔舐着薄薄的纸张,卷起的焦黑边缘急速蔓延,将那些带着血腥
气的图谋、那些指向汴梁大宋朝堂的毒箭焚烧殆尽。
顷刻间,密札便化为一撮轻薄的黑灰,飘落在他脚前的粗粝石地上。
未燃尽的火星在灰烬中明灭了一瞬,亦归于沉寂,只留下空中弥漫的短暂焦
糊气息。
「来人。」没藏讹庞的声音干涩沙哑,如同生锈的铁器刮过顽石。
一名身着西夏皮甲、面容隐藏在阴影里的心腹兵卒无声地闪入石室,单膝跪
地,静待吩咐。
「将此信。」
没藏从怀中取出另一封早已备好、同样蜡封的信函,递给兵卒,「务必亲自
交到汴梁城『聚宝斋』钱掌柜手中。不得经第二人手,亦不得拆看。若有半点差
池,提头来见。」
「遵命。」兵卒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双手接过那封似乎重逾千钧的信函,小
心收入怀中贴身处,再次无声地退了出去,融入石室外的黑暗甬道。
没藏讹庞枯坐灯下,火光将他嶙峋的影子投在凹凸不平的石壁上,扭曲拉长,
如同蛰伏的地底怪蟒。
他深陷的瞳仁里,仿佛倒映着千里之外汴京的巍峨宫墙、繁闹街市、暗流汹
涌的朝堂……嘴角,隐隐向上牵拉出一个冰冷的、几不可察的弧度。
李元昊这位殿下的棋,愈下愈险,却也愈下愈妙。
此番若能成事,则宋朝庙堂根基,又将摇动一分,殿下收服穆桂英一事,也
必将前进一大步。
石室重归寂静,只有外面传来的若有若无的痛呼和状似忍耐的撩人呻吟……
再说那汴京城内,朱雀门外。
虽值太平年月,贩夫走卒摩肩接踵,酒幡招展,丝竹盈耳,一派繁华盛景,
然则暗地里,总有那幽深府邸之内,秘事暗藏。
当朝太师庞藉府邸深处,一间暖阁陈设华美却不奢靡。
四壁书册罗列,博古架上玉器生光,俨然儒雅重臣之所。
然则此刻阁内气氛却沉凝如水。
檀香幽幽燃起,一缕淡烟攀缘而上,亦难驱散盘踞的肃杀之意。
庞藉坐在一张宽大的紫檀太师椅上,年过半百,鬓发微霜,一张脸保养得宜,
白净方正,眉眼间久居高位带来的雍容与深沉混杂着不易察觉的阴鸷。
他捏着方才由钱掌柜密呈而至的蜡封书信——那字迹狂放,正是没藏讹庞亲
书。
庞藉看得极为仔细,眉头时而紧锁,时而舒展。
信是用宋地白话书写,一目了然,却字字如针砭骨。
待到阅罢,他放下信纸,指尖在冰冷的紫檀木扶手上轻轻叩击,发出笃笃的
微响。
那平静的面容下,思绪却如急湍暗潮。
李元昊的心思,他岂能没有洞明?
佘太君一行不知所踪,自己前几日得密报,隐隐指向境外方向,如今李元昊
特意点明,无异于明示人质在手。
至于穆桂英与属下暗生情愫……哼,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即便是捕风捉影,
用在此刻,亦是妙哉。
此女悍勇刚烈,在民间声望极高,若有此污名加身,再煽动朝廷本就对杨家
叛国一事生出的忌惮疑惧,便是她浑身是胆、也是百口莫辩。
至于李元昊断言杨文广不成气候,这倒让他心中一块石头稍稍落地。
自己总有人走茶凉的一天,仇家后继无人,正合他的心意。
那设局的主意……庞藉眼底精光一闪而逝。
围点打援……驱虎吞狼……借刀杀人……环环相扣,竟是狠辣精准得要命。
由那小股西夏兵作饵,引动边境骚乱,料定其余宋军必然畏战不前,坐观成
败。
那好名惜才的八贤王赵德芳,岂能坐视穆柯寨陷落?必然跳出来请命穆桂英
戴罪平叛。
嘿,妙就妙在此时。
届时自己只需适时抛出那「暗生情愫」的流言蜚语,再点明穆柯寨经营日久,
形同坐拥私兵割据,此番西夏围而不攻专打朝廷兵马,岂非削弱朝廷对边境掌控?
如此一来,谁人又知这是不是穆柯寨和西夏演的一出戏!不如坚壁清野,让西夏
与穆柯寨火并……
一个可能失了名节、心怀怨望的妇人,与一群形同独立的寨兵……若能借西
夏之手除去,既可绝后患,省了朝廷动手的污名,又能极大削弱赵德芳在朝中的
号召力。
政争之事正是如此,一人进,就会有一人退。
那个手握金锏、太祖亲子的八贤王……这些年处处掣肘,是该好好敲打一番
了。
虽然不理解那李元昊为何总是抓着那杨家不放,但此计之下于己于国确实并
无损害。
一个元气大伤,人才凋零的杨家,哪里值得我庞太师计较,不过是和那李元
昊各取所需罢了。
至于陷害忠良的名声,呵!大丈夫生当五鼎食,死亦五鼎烹,不敢做桓温,
如何不能做主父偃!
庞藉沉吟片刻,指间的叩击声停。
他微微侧首,向侍立在一旁屏息凝神的儿子庞昱使了个眼色。
庞昱会意,悄然躬身退出暖阁。
不消两刻光景,侧门轻启,一阵香风率先涌了进来。
只见庞太师嫡女,当朝仁宗最宠爱的贵妃庞若雪,款步移入阁内。
她身量中等,却是生得玲珑有致,薄纱宫绡之内,腰如约素堪握,胸脯却丰
隆鼓胀出一道惊心动魄的弧度,其挺秀之势,竟将那薄薄的云罗撑显出极尽饱满
的浑圆印记。
下裳虽层层叠叠,但那宽而丰沛的雪股轮廓,依旧无法尽掩其极致的腴腆,
行动间,裙裾之下仿佛藏着两团浑圆的白玉脂膏,肉感沉甸甸地摇曳出无声波澜。
脸蛋儿是精雕细琢的端丽无双,肌肤白腻若初融新雪,一对剪水双瞳更是勾
魂摄魄,只是此刻那眼底深处潜藏的一丝机谋狡黠,令这天姿国色亦平添了几分
致命的危险。
「爹。」声音软糯娇媚,宛如清泉滑过丝缎。
庞藉并未起身,只示意了案上那封密信,「西夏那边来了消息。
你且看看。」他没有寒暄,直入主题。
庞若雪柳腰轻折,凑近书案,伸出葱管般的玉指拈起了薄薄的信纸。
她看得很快,眉梢眼底的风情随着信上字句悄然流转变化——惊诧、了然、
算计、狠绝……最终定格在一抹胜券在握的妩媚笑意上。
她阅罢,将信纸轻轻放回父亲手中,樱唇微启,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珠玑:
「爹爹以为如何?这步棋,确是绝妙。」
眼波流转,媚态中裹着冰霜般的决断,「八贤王爱惜羽毛,怜惜那穆桂英之
才,又自以为手握太祖金锏,总揽谏诤监察之权而矜傲自雄。此番穆柯寨有事,
他必作那仗义执言的君子状。只待他提了那贱人重掌兵权的话头……」
她微微一顿,眸光愈发灼亮锐利:「爹爹只需在朝堂之上,将李元昊信中所
言——无论虚实,只作流言汹汹、似有实据状,抛将出来。一个寡居守节却身染
桃色污名的寡妇,一个因丈夫『叛国』而备受苛责、心怀怨怼的悍妇,加上一个
拥兵自重形同自立的山寨。再将西夏围点打援专攻我朝军力的忧患点透。那坐在
龙椅上的官家,虽耳根子软,可最是忌讳此等威胁国朝根基之事。」
她轻轻嗤了一声,「如今杨家老幼不是流徙便是失落,只剩一根独苗杨文广
又不堪大用,早已不足为虑。然这穆桂英与穆柯寨,却是『尾大不掉』的变数。
朝廷能发落杨家满门,对这坐守边陲、军民一心的穆柯寨却束手束脚。如今西夏
愿做这把刀,父亲顺水推舟,正好借此良机剪除心腹之患,更可打压赵德芳日益
跋扈的锋芒。此一石二鸟,百利而无一害。」
庞藉捋须点头,眼中尽是嘉许的笑意:「吾女聪慧,深得吾心。
此事关键,却在陛下最后那一念之间。」他话锋一转,意有所指。
庞若雪了然一笑,娇媚天成中带着一丝冷绝的妖冶:「爹爹放心。待那朝议
纷争、龙心惶惑、摇摆难定之夜,自有女儿,将那临门一脚……轻轻补上。」
她葱白玉指轻轻抚过案上古琴紧绷的丝弦,发出极轻微却又极清晰的铮鸣。
汴京城的街市依旧嘈杂,人潮涌动,贩夫走卒的吆喝不绝于耳。
可没过几日,一种无形却沉重的阴霾,渐渐笼罩在有心人头上。
消息初起,只在几家深门大户的低语中流传。
接着,便像是投入了滚烫油锅的一滴水,轰然炸开,迅速蔓延至街肆坊间:
「听说了吗?天波府的佘老太君……杨家的那位定海神针……在前往穆柯寨的路
上……不知所踪了。」
「什么?消息确凿?」
「千真万确。有西边回来的商队亲眼所见,只说遭到了『强人』袭掠。」
「强人?哪路的强人敢动天波府的队伍?怕是……」
担忧、猜测、惊惶如野草般在汴京坊市疯长。
又过了不到一旬,更大的惊雷伴随着六百里加急的边报,炸响在皇城司的门
槛前。
八百里秦川古道,烽火连天。
西夏骑兵如一股股刮过草原的黑色旋风,越过那被视为壁垒的险要关隘,竟
直扑向边境一个并非重要军镇的方向——穆柯寨。
消息传到民间,瞬间点燃了早已绷紧的民情。
茶肆中、酒楼里、街角处,人声鼎沸:「西夏豺狼又来了。烧杀抢掠,无恶
不作。」
「这次怎地绕开州府不打,专冲着穆柯寨去了?」
「穆桂英。是杨门女将穆桂英。她还在穆柯寨。」
「西夏人恨杨家入骨。此番怕是冲着赶尽杀绝来的。」
「朝廷该发兵救援啊。穆元帅当年可没少杀退西夏人。是为国立过大功的。」
「哼。立大功?你没听说吗?杨家男的可是一窝子叛国贼。杨宗保就临阵反
了水。有其夫必有其妻。谁又能说得准?再说那穆柯寨孤悬在外,听说那穆桂英
寡居寂寞,准早就和她寨子里那些光膀子汉子眉来眼去了。朝廷若派兵,岂不是
去救一对……」有那早被收了钱的闲汉刻意压低却又引人耸听的声音在角落响起。
「放你娘的屁!」
立刻有粗豪的汉子拍案而起,怒目圆睁,「穆元帅何等英雄,镇守边关多少
次把西夏贼寇杀得屁滚尿流?岂容你等鼠辈在此污蔑!」
「就是。杨家满门忠烈,多少男儿血洒疆场?那杨宗保叛国之事扑朔迷离,
谁知是不是遭人构陷?佘老太君等人无故失踪,这其中没鬼?如今西夏摆明了冲
着唯一能打的杨门血脉穆元帅去了。朝廷若不救,岂不让天下忠勇之士寒心?!」
「话可不能这么说。那穆柯寨自立门头已经多少年了?俨然是个小朝廷。朝
廷的法度在山寨里行得通几分?说是杨家姻亲,可兵是他们的,粮是他们的,将
是他们的,除了名义上归宋,与割据藩镇何异?前唐殷鉴,犹不远矣啊。此番西
夏兵围点打援,专打我朝廷援军,分明是要借机削弱朝廷力量,让穆
柯寨彻底坐大。到时穆桂英一声号令,说自立投敌,谁人能挡?」
「没错。谁知道是不是那穆桂英心怀怨恨,私下勾连了外族,弄出这苦肉计
来骗朝廷出兵帮她火中取栗,反噬朝廷?」
「胡扯!简直是一派胡言!穆元帅忠心天下皆知。」
「知人知面不知心哪。一个女人,守孝多年,手握重兵……哼!」
民间舆论已沸,朝堂之上更是风雷激荡。
偌大的金銮宝殿,此时剑拔弩张,几乎要掀翻了穹顶。
八贤王赵德芳,这位太祖皇帝的嫡亲血脉,虽已年逾耳顺,然英气不减当年。
他头戴玄冠,身着紫蟒袍,手持象征太祖遗命、可上打昏君下责佞臣的金锏,
立于丹墀之下,腰杆挺直如同沙场的长枪。
他目光如炬,朗声奏道:「陛下。西夏不宣而战,兵锋直指我大宋边民。穆
柯寨虽为江湖之地,然寨主穆桂英系杨门嫡媳,为我大宋立下过赫赫战功。其部
曲多年抗击西夏,守土安民。此值家国危难之际,敌寇肆虐之时,岂可坐视孤寨
陷于豺狼之口而朝廷不发一兵一卒?臣恳请陛下。即刻下旨,赦免穆桂英待罪之
身,由其统领附近府军及自发义军,以迅雷之势反击西夏。一则扬我大宋国威,
震慑不臣;二则解穆柯寨之围,保我臣民。此举上应天心,下顺民意,望陛下明
鉴。」
声音如同洪钟大吕,在殿宇间回荡,许多武将脸上露出感佩振奋之色。
然而话音刚落,殿内那老成持重如岳峙渊渟的太师庞藉,不慌不忙地踏前一
步,躬身行礼,他声音不高,语速平缓,却字字带着千钧之力、浸透骨髓的寒意:
「王爷忧心国事,拳拳之心老臣感佩。然,」
他话锋一转,似带着无限惋惜与隐忧,「军国大事,非同儿戏,尤须审慎查
察,明辨主次。臣近日亦闻军报,西夏此次出兵,虽号称数千精骑,实则虚张声
势,主力并未越过我朝早已筑垒成墙的重镇险关。他们围住了穆柯寨,却并不急
于攻打,其主力反倒在我各卫所援军必经之路频频袭扰设伏。意图为何?此乃
『围点打援』之毒计。是要以穆柯寨为饵,诱我朝廷大军前赴,然后趁其疲惫分
路设伏,以求在平原旷野之上,削弱乃至歼灭我增援之精锐。」
庞藉抬起头,目光如霜刃般扫过八贤王,沉声道:「此其一。
再者,老臣不得不提那穆柯寨……恕臣直言,此寨自穆羽老寨主创立,众人
拥立,号「穆天王」,后为穆桂英经营,已历两代,数十年矣。
其拥精兵数千,粮秣自足,城坚寨厚,法令自设,军卒只知有寨主,不知有
朝廷。
名义上归附,然形同割据一方。
穆桂英身为朝廷侯爵,夫家又犯下叛国弥天大罪,获罪于朝廷,其本应深居
简出恪守本分,静待朝廷法断。
然其退守穆柯寨后,非但未尽分毫收敛请罪之意,反而似有加固城防、扩招
兵员之举。
此番西夏猝然相攻,兵锋所向,时机选择……岂不蹊跷?更兼坊间传言纷扰
……」他刻意停顿了一下,眼神显得凝重无比,「或有捕风捉影,言道其夫亡寡
居,于寨主之位统领男丁日久……难免有瓜田李下……暗生情愫之嫌……虽未入
罪,然民心已有疑虑。
此等情形下,其是否真如八爷所言,心怀忠君报国之念?抑或因身陷罪名而
心生怨怼?其麾下兵马,是否会为朝廷所用?抑或只效忠于穆寨主?老臣实不敢
妄自断言。」
他再次深深一躬,声音恳切却如重锤砸在仁宗心坎:「陛下。
若朝廷此刻贸然派遣大军救援,耗费钱粮无数、兵卒血肉之躯姑且不论,倘
若此女果真心怀异志,与西夏内外勾结,演一出苦肉计,那我增援大军岂不是自
投罗网、腹背受敌?届时非但救援不成,反使将士沦为鱼肉。
这后果之惨烈,非我大宋所能承受。」
他抬起头,眼中精光一闪而逝,抛出最终的狠棋:「依老臣愚见,不若反其
道而行之。
既然西夏觊觎的是我增援之军,穆柯寨又形同独立王国。
那便传令各处官军卫所,只加强险要关隘守卫,谨防西夏主力乘虚叩关。
至于穆柯寨方向……施行坚壁清野之策,将邻近寨子的军民尽数撤入坚城之
内。
既然西夏人如此『好意』地替我们去扫清那个朝廷多年想动而碍于颜面情分
又不好动手的『隐患』,倒不如……」他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顺水推舟,
隔岸观火。
让那如狼似虎的西夏军,去替朝廷『试探』一下穆柯寨的忠诚与实力。
若穆柯寨万众一心浴血奋战,挫败强敌,那自然是忠于朝廷、勇于担当的铁
证。
陛下不妨再予以褒奖安抚以安其心,朝廷威信无损,更可得一强援固守西陲。
若……他们不敌溃败,或被西夏所灭,或选择从了西夏……」他冷哼一声,
话中寒意砭骨,「那不过是证明了其早有异心或实力不济,朝廷亦省去了一个心
腹之患,更借此昭告天下有异心者,不念朝廷体统、行割据之实者,便是如此下
场。
此乃一举数得、以静制动的上上之策。
望陛下……明断乾坤。」
「庞藉。
尔……尔敢妄揣忠良,信口雌黄!」八贤王须发怒张,手中金锏直指太师,
声若雷霆,「穆元帅为国血战之时,尔等尚不知在何处安享太平。
杨家满门忠骨埋在疆场。
此等污蔑构陷,岂是士大夫所为?分明是坐视忠良被戮,行那亲痛仇快之事。
更欲借此打压异己,其心可诛!陛下,万万不可听此祸国之言!」
「王爷。」庞藉不卑不亢,针锋相对,「此非老臣一己私见,而是为社稷安
危计,为万千军士性命计,为朝廷纲纪计!岂能将我大宋精锐,置于一个名节存
疑、立场难明的戴罪之身手中?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岂能如此轻率?至于杨家过往忠烈与否……功过自有后世评说。
然今日之事,关乎当前之国策。
容不得半分私情。
王爷怕是爱才心切,恐为情所蔽,反中敌寇奸计。
陛下圣明烛照,当知其中轻重。」
殿中双方唇枪舌剑,势同水火。
仁宗皇帝赵祯高踞龙椅,眉头紧蹙,脸色白一阵红一阵。
一面是皇叔据理力争,慷慨激昂,以国威民心为说辞;一面是国之重臣老谋
深算,字字不离社稷安危、朝廷利益,处处点中他内心最深的疑惧与忌讳。
他欲反驳庞藉,又觉得其所言似乎稳妥;欲支持赵德芳,又怕真如庞藉所料
酿成巨患。
尤其那「穆桂英心怀怨怼」与「穆柯寨形同割据」的利刃,一次次精准无误、
不疾不徐地切割着他那本就犹豫不决的心弦。
满朝文武鸦雀无声,目光俱都聚焦在御座之上,连呼吸都屏住了一半,唯恐
错过圣心丝毫的偏移。
朝堂内外的空气,仿佛凝固成一块巨大沉重的冰坨子,压得人喘不过气。
这一日的朝会,便在剑拔弩张又诡谲难言的死局中勉强落幕,未能议决。
是夜。
九重宫阙深处,椒房别院。
月光透过轻绡宫纱,映在描金剔红的妆台上,也映着庞贵妃一张精心养护、
艳若桃李的脸庞。
宫苑内的奇花异草吐纳幽香。
她一身浅碧色薄绸寝衣,那丰满到足以令金吾侧目的傲然胸乳将前襟绷显出
一道惊心动魄、浑不似人间能有的饱满曲线,顶端两抹深壑在幽暗烛光下若隐若
现。
窄软的腰肢束以轻柔丝绦,纤韧欲折。
寝衣下并无重裙,其下身段的丰盈轮廓毫无遮掩,尤其从后腰至玉臀的曲线,
宛如精心塑成的白腻山峰,宽厚而腴美,沉甸甸地坠出两团令人心荡神驰的绝世
峰峦。
莲步轻移间,股肉微微颤晃,那惊心动魄、充满原始生命韵致的丰腴颤意,
便是最严苛的礼法官在此,也难免多看一眼那亵越宫规的美好弧度。
她捧着一只玲珑嵌玉的鎏金汤碗,步履轻盈地行至御榻之前。
汤盏里盛着温热的冰糖雪蛤莲子羹,蒸腾的热气带着甜香,缭绕在她粉雕玉
琢的颈侧耳垂。
榻上的仁宗刚从繁冗的朝议中脱身,此刻正斜倚着金线蟒纹的引枕,揉着发
胀的额角,眉心紧锁。
「官家……」庞贵妃声音甜腻得如同浸了花露,轻轻坐上榻沿。
那惊人的臀肉随着她落座的姿态,沉甸甸地陷入软褥之中,又因那柔韧十足
的弹性,微微向四周延展出饱满丰盈的光晕,寝衣紧贴处,弧线勾魂摄魄。
她将玉碗送至仁宗嘴边,纤纤玉指拿起调羹,姿态优雅又体贴。
「白日朝堂议事实在惊心动魄,伤了神思。快用些羹汤定定神。」
仁宗就着她的手啜了一口,温热甜润的汤汁滑入喉咙,稍缓烦忧。
他叹息一声:「爱妃啊,这穆柯寨之事……朝上纷议汹汹,实在是难以决断。」
庞贵妃放下羹碗,抬起柔若无骨的皓腕,用温软的指尖轻轻揉按仁宗的太阳
穴,动作娴熟。
她微微倾身,饱满的胸乳几乎蹭到仁宗的臂膀,温热的馨香包裹着帝王。
「妾身一介女流,不敢妄议前朝政事,」
声音放得极轻极柔,如同枕边呢喃,带着些许委屈又识大体的娇态,「只是
……只是看着官家忧心如焚,妾身这心里也七上八下……想到那八贤王……」
她巧妙停顿,似是无意提起,美目中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锋芒。
「他今日在朝堂之上,手持太祖金锏,言辞激烈……似乎有些过于……咄咄
逼人了。」
她叹了口气,指压动作未停,眼神带上几许迷惘与忧惧,「那金锏之威……
唉,妾身每每想起便心惊肉跳。太宗皇帝传下它,自然是赋予宗庙社稷之重托。
可……可王爷身负太祖血脉,又掌如此神器……这些年每每遇事则直言强谏……
对官家的圣裁,也……也时有争持……」
她小心翼翼地看了仁宗一眼,见他并未动怒,反而眉头蹙得更深,才接着用
那气若游丝、仿佛只诉与榻上情郎听般的声音,低低道:「妾身有时……夜深人
静想起那金匮盟约前事……便止不住地害怕……」她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仿佛
深陷噩梦,那双会说话的眸子里盈满了惊悸的泪光,「官家您是太宗皇帝嫡传的
龙子,承的是天授的正大统序。可……可太祖当年亦是传位于弟才留下那金匮之
盟……每每思及于此……」
她声音哽咽,更显楚楚可怜,「妾身只是忧心官家。忧心这大宋的万里江山。
若事事都由八贤王执了金锏说了算……那圣上……这天下究竟系于谁人?」
这番话如同淬毒的冰针,轻柔却无比精准地刺入了仁宗心底最深的角落。
那丝早已盘踞多年的、难以启齿的、基于金匮之盟阴影的忌惮与恐惧,瞬间
被无限放大。
太祖之死、兄终弟及的历史、八叔手中的金锏……这一系列联想组合成的恐
惧,远远超过了此刻边境穆柯寨的得失,更深沉地压在了赵祯的心头。
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一股寒意从脊椎骨升起。
「够了。」仁宗猛地低喝一声,挥开庞贵妃的手,脸上阴云密布。
他并非喝斥爱妃,而是那骤然爆发的对自身权威的强烈恐慌与不安。
庞贵妃这看似关切、不着痕迹的「忧虑」,恰如一瓢滚油泼在了本就暗火丛
生的薪堆之上。
庞贵妃立刻噤声,盈盈起身,跪俯在榻前,云鬓微乱,体态显得更加楚楚可
怜,玲珑曲线在跪姿中愈发抖落惊心动魄的饱满与委屈:「陛下息怒。是臣妾多
嘴了。臣妾妇人之见,胡言乱语不识大体……」
她深深叩首,额头几乎触地,肩背微微颤抖。
那惊心动魄的腰臀线条在伏低的姿态中构成一弯极其夸张的、蕴含了巨大绵
软弹力的硕美弧线,带着无声的娇弱哀求之意。
仁宗看着跪地的尤物,心头的火怒与那丝被触及敏感地带的惊悸纠缠着,最
终化为一声不耐烦又意蕴不明的冷斥:「后宫切勿干政。这等话,休要再提。」
「妾身知罪。」
庞贵妃如蒙大赦,又惊又喜地抬起头,泪光莹莹中带着无限的信服仰慕,
「官家……妾身知道错了……」
她膝行一步,柔若无骨地倚在榻边,重新将那碗温热的羹汤端起,乖顺地奉
上。
只是方才那番诛心之言,已如毒蛇噬髓般,牢牢印在了仁宗心头最敏感的所
在。
次日早朝。
龙椅之上,仁宗的神色似乎比昨日更显疲惫憔悴,眼下带着微青。
他目光扫过阶下,刻意避开了八贤王那殷切又锐利的眼神。
朝堂之上再次陷入关于穆柯寨与西夏兵锋的廷议激辩。
八贤王依旧据理力争,激昂慷慨,字字掷地有声。
庞藉一派则反复申明「保存实力」、「防范内患」、「以夷制异」之利。
待到双方辩无可辩,仁宗沉默良久,终于开了金口,声音带着一丝难以掩饰
的沙哑与疲倦:「众卿所言……朕已细思。事关重大,牵涉国本安危,不得不慎
之又慎。」
他微微一顿,殿内落针可闻。
「穆柯寨……」
提到这个名字,仁宗眼神闪过一丝复杂难辨的光,「穆桂英虽承其父旧业,
又曾立战功,然其夫杨宗保犯有重罪,其身为待罪之臣妻室,身份敏感。加之地
处边陲,兵员复杂。值此西夏兵锋汹汹而来之时,贸然大举增援,恐堕敌围点打
援奸计之中。此其一。」
「其二。」
他避开八贤王灼灼的目光,语速加快,仿佛急于摆脱某种无形的压力,「穆
柯寨城坚寨深,兵勇尚在。值此国难之际,正需其上下同仇敌忾,固守家园,以
彰忠烈,亦为朝廷分忧。」
他深吸一口气,最终定下调子:「颁朕旨意:明旨褒扬穆柯寨众将士守土抗
敌之功。」
「命邻近州府官军,固守险要关隘要冲,绝不可使西夏一兵一卒得以突破防
线南下,威胁百姓安宁。然……非奉明确诏令,不得擅离驻防之地,随意出击浪
战。更不可赴援穆柯寨,堕敌奸谋。」
「令穆柯寨寨众,戮力同心,固守疆界。待其自保成功,朝廷……自有后续
安抚,钦此。」
这旨意一出,殿内群臣反应各异。
八贤王面如死灰,手握金锏的指节捏得发白。
那最后那句「待其自保成功,朝廷自有后续安抚」,听在他耳朵里,与判了
穆柯寨上下无援待毙的死刑何异?这分明是采纳了庞藉隔岸观火、坐视自生自灭
的毒计。
甚至,还裹上了一层褒奖守土的糖衣。
其无情之至,何其寒凉。
庞藉一派,则是眼观鼻鼻观心,垂首恭贺圣裁英明。
庞藉本人心中雪亮,昨夜那双纤纤玉手点下的「棋眼」,已然生效。
陛下心中那只名叫「猜忌」、「忌惮太祖一脉夺权」以及「对割据势力深深
戒备」的猛虎,终于在庞贵妃那滴「忧惧之泪」的催化下,挣脱了最后一丝人情
束缚,咆哮而出了。
旨意如风,迅疾地自崇政殿传出,由门下省覆核,再由内侍誊写盖上天子玉
玺宝印。
随即,一骑披着朝廷紧急边报绶带的传旨使者,马蹄扬尘,在薄薄的晨曦中
冲出巍峨的汴梁西华门。
马蹄踏碎了官道上凝结的薄霜,一人一骑,绝尘向西。
目标只有一个——远在数百里之外,或许此刻已被战云笼罩的穆柯寨。
这位不知使命轻重的传旨使者,并不知道怀中这道贴着冰冷鹞羽、火漆封口
的诏书,将会在数日之后,如何残酷地撕裂千里之外一束坚守的信念,又将这滚
滚狼烟的走向推向何等血腥残酷的境地。
他只知道,要鞭打快马,奔向那片即将迎来最终拷问的战火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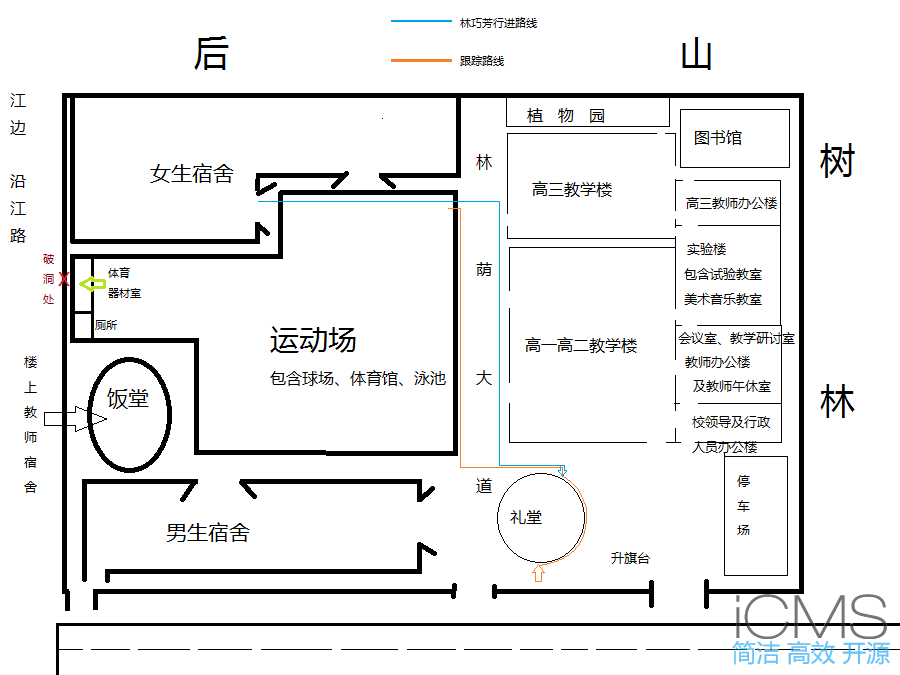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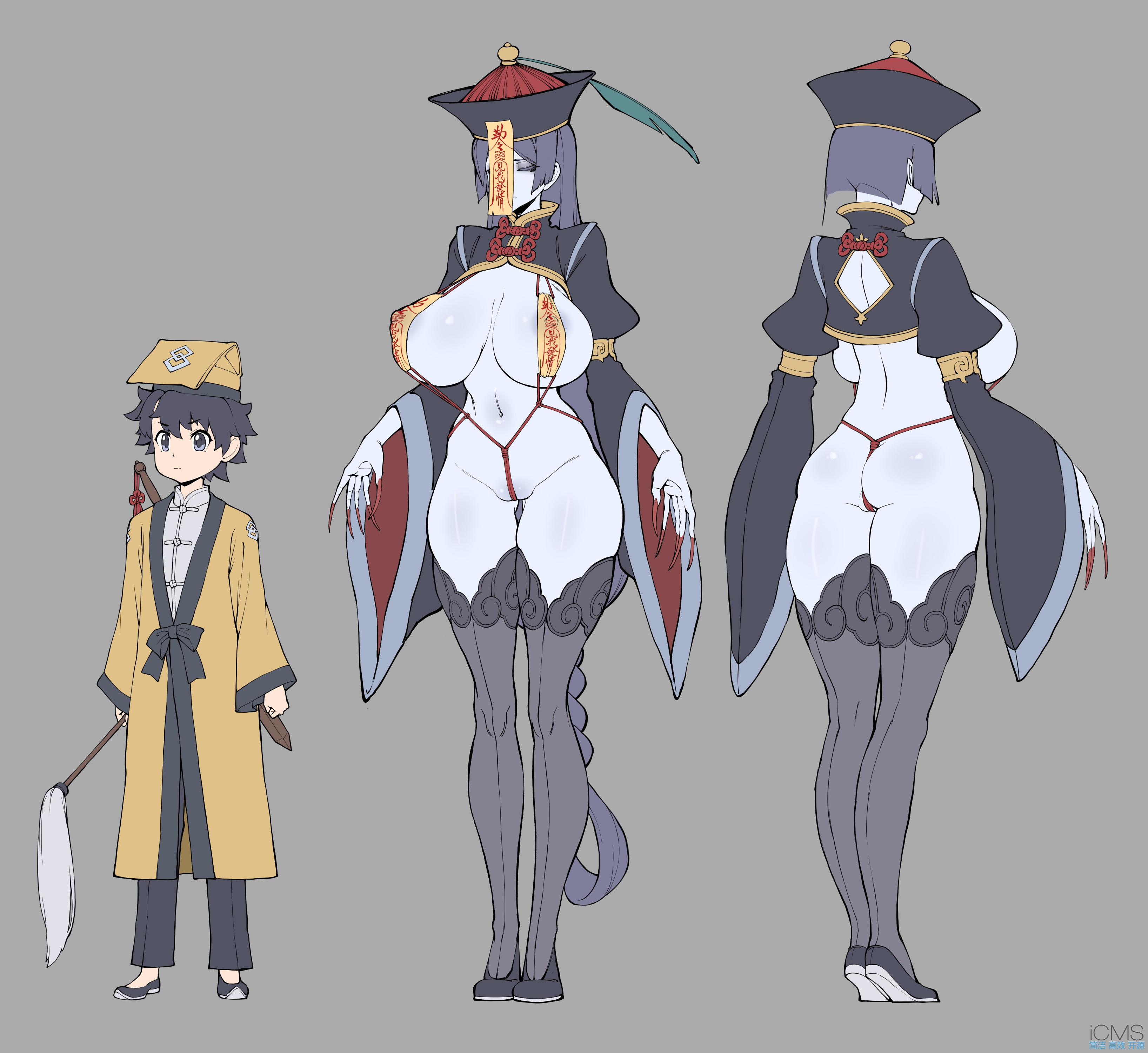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